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明代杜诗学中的学杜与变杜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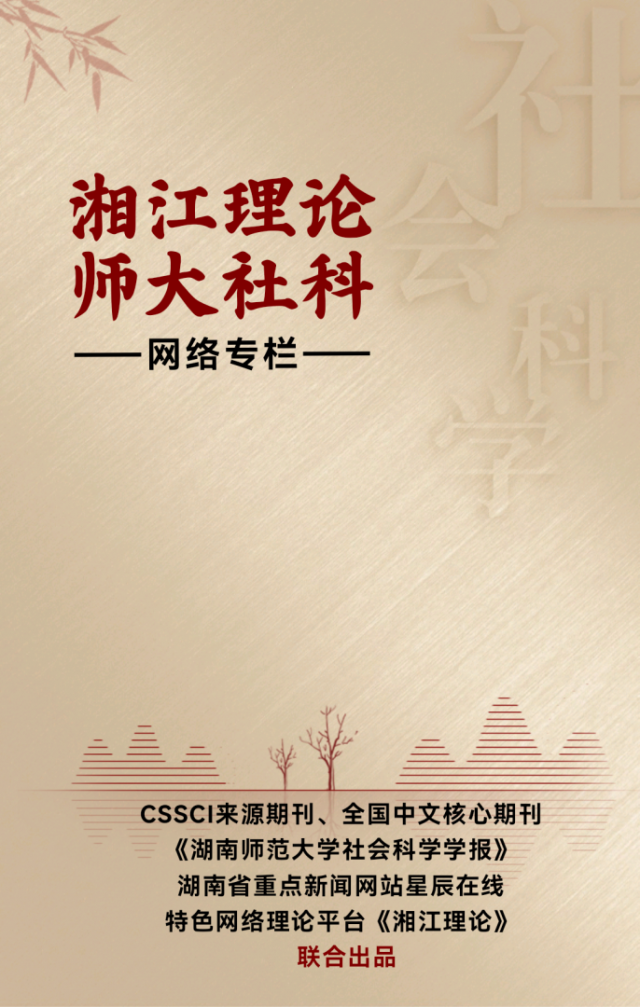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雷 磊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与文献。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韵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刊》主编等。湖南省“芙蓉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湖南省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专家,湖南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家。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1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各1项。主编的《杨慎全集》先后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和《2021-2035全国古籍工作规划》首批重点出版项目。出版专著2部,参编著作6部,参编教材3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臧 洁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明代杜诗学中的学杜与变杜
——以杨慎评点张含诗歌为中心
核心提示
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其中杜诗学是明代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力。前后七子派专宗杜诗,颇有模拟之习。反思宗杜之思潮渐起,杨慎、张含即为代表。张含前期受前七子派影响,专力学杜,至有杜甫后身之誉。后期同杨慎密切交往,两人互相影响,发生由学杜至变杜之演进。杨慎的张含诗歌批评核心是探讨学杜问题,由此而主张不仅应以杜学杜,更应以古变杜,提出 “翻用杜语,新若己出”等说,强调充分吸收古代诗歌资源,特别是吸收历来被忽视的六朝诗歌艺术,以此为阶梯,上溯至《诗经》,领会精神,表现真情,批判现实,成就当代真我之风诗。杨慎围绕张含诗歌批评提出的一系列文学观点是对《升庵诗话》的发展。
内容精选
宋元明清之杜诗学均为显学,明代杜诗学于前七子派至后七子派复古思潮汹涌时最为兴盛。可以说,杜诗学是明代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力。代表明代文学主流的前后七子派主张“古体汉魏,近体盛唐”,而盛唐“最李杜”,实则最杜,即于近体专力学杜。即使在前七子兴盛的时期仍有反思宗杜的声音,在前七子派分散和消歇之时,这种声音逐渐扩大,杨慎、张含等人即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用六朝来弥补杜诗之不足,同时强调诗歌的情感性和个性化。此一股思潮颇有影响,也是合力推动明代杜诗学发展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不可忽略。而学界对此关注甚少。
杨慎在京城时期同前七子派有交往,张含约于此时亦学诗于前七子派领袖李梦阳,以杜为志,至有杜甫后身之誉。杨慎被贬云南后,与张含诗学交游甚密,张含赠诗杨慎达千首之多,两人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张含深受杨慎影响,诗学思想发生由学杜而变杜的转变,成为“杨门六子”之首。张含诗歌多由杨慎选评,现存三种:一是嘉靖二十七年序刻《张愈光诗文选》八卷,二是嘉靖二十八年序刻《张禺山戊己吟》三卷附一卷续一卷,三是嘉靖三十九年刻《升庵选禺山七言律诗》一卷。杨慎上述文本中关于张含诗歌的评点有二百余条,乃精心结撰而成,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学杜与变杜,反映的是杨慎晚年成熟期杜诗学观念。因此本文即从杨慎的张含诗歌批评这一角度探讨明代杜诗学的新发展。
一、工逼少陵
张含弟张合序其兄诗集《弁乙未鸣》一文有云:“禺山伯兄早厌时业,诗以杜志。”张含赴京应试,结识并师从前七子派李、何等,转而专力学杜,而厌弃时业,仅以举人终身。可谓前七子派之外围人物。李梦阳就认为张含是“其为诗杜”,即其诗学宗尚杜诗。同时交游文士亦称许张含“诗篇似少陵”。张含不仅受到前七子派的影响而学杜,也有家学的熏陶,曾玙《序升庵选禺山七言律》云:“厥考司徒南园公……诗律已传于世,唐杜少陵父子可比迹云。”是以张志淳、张含父子比附杜氏父子。张含所学主要是杜甫律诗,杨慎《跋乙未鸣》云:“予每爱禺山子近体格诗合作,固少陵家之鲁男子也。”华云《禺山律选序》亦云:“禺山之律,效法盛唐,而得少陵风骨,盖天下之选也。”因此,同为“杨门六子”之一的李元阳遂称誉张含为杜甫后身。总之,张含专力学杜乃为当时公论。
张含在诗歌中也常以杜甫自比,如“肯覆杜甫掌中杯”(《登台》)、“少陵何事湿衣裳”(《遣兴》)、“多愁杜甫苦耽诗”(《得升庵东归消息》三首其三)、“堪笑穷愁杜甫诗”卷四(《读书》二首其二)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张含与杨慎乃诗坛挚友,张寄杨诗往往以杜甫自拟,而以李白代指杨慎,如“杜甫空怜李白才”(《己亥秋月寄升庵》),即是如此。又如张含《绝句九首寄升庵》其五云:李杜有诗相寄赠,翰林颇少拾遗多。固知二老无他意,后学相疑将奈何。
此诗即以李指杨慎,杜指张含,杨慎评点云:“此二十八字诗话也。”张、杨互赠诗歌千余首,而张多杨少,确为诗坛佳话,也为亦师亦友之佐证。张诗又有自拟杜甫,而以扬雄代指杨慎者,如《寄升庵》:“吟诗有客须逢甫,献赋何人肯荐雄。” “甫”指杜甫,“雄”指扬雄。慎与雄通姓、同乡,且均为博学之士,代指颇切 。
张含多有学杜之作,仅举数例说明。如《点苍书院次林白石韵》,杨慎评曰:“与杜陵《终明府水楼》同调。” 张含此诗与杜甫《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一同韵,可谓同调之一证。又张诗有“万里衣冠开六诏,百年词赋效三湘”一联,句法显然效法杜诗 。又如张含《太华寺》写登寺所见景象,杨慎评曰“此诗全似少陵” ,其“诸天不在藤萝外”句系反用杜甫《涪城县香积寺官阁》“诸天合在藤罗外”句。
又如张含《即景》六首,杨慎评曰:“少陵遗意,在《竹枝》《漫兴》之间。”杜甫有《绝句漫兴》九首,系作于上元二年(675)春客居成都草堂之时,《杜臆》云:
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
“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之论或本于上引杨评。张诗则可谓目之所见,率然而成。杨慎有“比兴,景也”之说,绳之杜诗《绝句漫兴》,亦为即景而兴感者,张诗《即景》即效法杜诗这一写法,不过一重兴,一重景而已。可举此两组诗第一首作比较: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一)
幽亭独坐朱明天,唶唶闲读古苔篇。南塘荷花太稀少,北塘莲叶特新鲜。(张含《即景》六首其一)
两诗写景,而景物皆著我之情思,杜甫为客愁,张含则为闲适。《杜臆》以为“‘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领”,则“闲”之一字亦为《即景》六首之诗眼。可见,张含于章法颇效杜诗。须特别提出的是,《即景》第五首系效法《绝句漫兴》第七首一句一绝之篇法: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
萱草葵花媚小园,石榴金竹护幽轩。斑鸠白鹭频来坐,垂柳牵风细细翻。(张含《即景》六首其五)
《张愈光诗文选》刻于嘉靖二十七年,而此前一年刻有张含选辑、杨慎批点的《唐诗绝句精选》四卷《拾遗》一卷《附刻》一卷,其《拾遗》有张含跋语,引杨慎之言曰:“古绝以一句一绝,其本色也,如‘春水满四泽’是也。”可见,张含、杨慎在创作、评论效法杜甫《绝句漫兴》的《即景》之时似已有一绝一句绝句体式之理论自觉。此后,杨慎对一句一绝之体式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其《升庵文集》卷五十七“绝句”条云:
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是也。或以为陶渊明诗,非。杜诗“两个黄鹂鸣翠柳”实祖之。王维诗:“柳条拂地不忍折,松柏稍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猱子,柏叶初齐养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散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皆此体也。乐府有“打起黄莺儿”一首,意连句圆,未尝间断,当参此意,便有神圣工巧。
此条诗话实本于宋张端义《贵耳集》之论,仅补充杜甫、王维、欧阳修三首诗例。但杨慎此条诗话后收入明焦竑所编《升庵外集》“诗品”部,又再收入清李调元所编《升庵诗话》。而仇兆鳌《杜诗详注》于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下即引用的是杨慎此条诗话,以此为依据认同此首属一句一绝体。可见,杨慎关于一句一绝之绝句体式观点影响更大。又由所举杜甫《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之例可知,杨慎、张含明了杜甫绝句有一句一绝体式。因此,我们认为,张含《即景》六首其五效法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之观点似可成立,而杨慎“少陵遗意”之评对此颇有提示作用。
又如张含《颍川侯祠》,杨慎评曰:“此诗可配杜工部《诸葛祠》一诗。”全诗如下:
野老争传傅颍川,当时功业冠南滇。平蛮营垒苍山外,破虏旌旗白石边。只见荒祠通落日,不闻遗像照凌烟。阴风古树无穷恨,常为英雄吊九泉。
“杜工部《诸葛祠》一诗”指名作《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张诗立意、格调系效法杜诗,然无论写景、叙事、议论,张诗之情韵均不如杜诗。恐怕系为杜诗所笼罩而无法出脱所致,可作学杜者之炯鉴。
除上述四例外,张含学杜之作尚多,仅以杨评为例,就有“咄咄逼杜”(《寄升庵长句八首》尾批,又《长安旅夜》尾批)、“格调则杜”(《寄董大守宗兗》尾批)、“工逼少陵”(《送谯云阿表使北上五言格诗三十韵》尾批)等批语。综上可知,张含诗歌系曾从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立意、格调等方面效法杜甫。
二、翻用杜语,新若己出
嘉靖四年,杨慎贬谪至云南,开启与张含密切交往的新阶段。以杨慎为领袖的六朝派诗学思想逐渐成熟,其作于嘉靖十一年的《张子小言序》有对前七子派末流学杜风气之弊病的激烈批评:
后之人曰:诗必谨体裁,崇师范。若金科,若玉条,若嘉量,若懿律。否则曰是非裁也,是非体也。此非过乎风人之言,不及乎风人之言也。多效法乎少陵,抉其片言,摘其坠文,命之曰“聚敛”;衣被而缀合之,命之曰“拆洗”。“聚敛”也,“拆洗”也,今之弊乎?与夫生吞也,活剥也,古之弊一也。
“后之人”乃指前七子派及其后学,“后之人曰”者乃前七子派模拟主张。杨慎强烈反对聚敛拆洗式、生吞活剥式的模拟杜诗风气。但是,杨慎并不全盘反对学习杜诗,此序又引张含的话说:
张子曰:所欲学杜者,不矜于形而矜于神。执者拘之,为者败之,罔象乃可得玄珠,希其难乎!
杨慎在一定程度赞同张含此一化杜主张,这大概是对效杜思想的发展和提升,有其合理性。上节所引张含《即景》六首其五学杜诗一句一绝体,似可谓“不矜于形而矜于神”者。华云《禺山律选序》认为张含学杜是“师其意不师其迹,法其调不法其辞”,与张含学杜主张略同,“师迹”“法辞”大概属“矜于形”,“师意”“法调”属“矜于神”,而上节所引张含《颍川侯祠》诗艺术成就虽难以比肩杜诗,但其学杜情形似可当得此评。
但是也有师其辞而新其意的情况,也可划入化杜(“矜神”“师意”“法调”)之列。可举一例说明。张含《独酌》云:
冬孟三巴水势降,绝无惊浪溅蓬窗。黄昏露湿黄鱼岭,白昼烟迷白马江。隔滩鹭鸶还个个,眠沙鸡鶒故双双。浊醪自注磁罂好,无谢琼苏玉作缸。
杨慎尾评曰:“翻用杜语,新若己出。”“眠沙鸡鶒故双双”当翻用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鸡鶒双双舞”句,但是二句字数、用法、情境、主旨均异,即以情境、主旨而论,杜为孤困,张为闲适。“双双”与“个个”之组合颇有物化而逍遥之意。
又张含《近事》三四句云:“海沤作伴我何虑,江草唤愁他日生。”“江草”句当用杜甫《愁》首句“江草日日唤愁生”语,但系反用其意,大概是说任他江草日日唤愁吧(而与我何干),也算是新意之情形。“沤”通“鸥”,“海沤”当用杜甫《巴西绎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其二“还同海上鸥”句之意,而语颇异。两诗“海鸥”均出典于《列子》,取心和形顺意。杨慎评点张含《近事》说:
三四用杜,妙甚。用杜而不为杜用,乃作手也。
三、四句确均用杜,但用杜的方式有所不同,一则为用意而新辞,一则为用辞而新意。若用杜辞、意全同,就属“为杜用”之列;若辞、意有同有异,则属“不为杜用”之列。显然杨慎提倡用杜而不为杜用这一辩证诗法,要求学杜而为我所用,诗歌创作见出作者自家面目。张含的“矜杜之神”论与杨慎“用杜而不为杜用”皆同一旨趣,其目的都是要求诗歌创作“新若己出”,是反拨前七子派模拟论而提出的更高诗学追求。
“不为杜用”推延开去,就是“不为人用”,这就与杨慎一贯主张的“夺胎换骨”这一诗法相通了。杨慎《升庵诗话》“杜诗夺胎之妙”条,云:
陈僧慧标《咏水》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沈佺期《钓竿篇》:“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虽多二字之句,而壮丽倍之。可谓得夺胎之妙矣。
杜诗也是用前人语,可以说杜诗达到了用人而不为人用也即夺胎换骨的艺术高度。因此,杨慎甚至认为“杜诗之妙,在翻古语”,那么今诗之妙也有在于翻杜语者。又由前所引杨慎评张含诗歌“翻用杜语,新若己出”之语可推知,所谓“翻杜语”即是“用杜而不为杜用”,达致“新若己出”之诗境,这也属于“夺胎换骨”。
若作进一步分析,上引杨慎《升庵诗话》“杜诗夺胎之妙”,系杜诗用人语而新其意之例。此诗题为《小寒食舟中作》,作于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春漂泊潭州之时。正如杨慎所言,“春水船如天上坐”句系用沈佺期诗句而增“春水”二字,“而壮丽倍之”。参互上下文言之,所谓“丽”倍之,当指杜诗写景更明艳,用语更为精工。所谓“壮”倍之,则意绪更为萧瑟沉郁。黄庭坚称之为“触类而长之”,方回则认为是“公加以斤斧,一变而妙矣”。林时对则有解释:“‘春水’二句,非袭用前人句也,此用前人句,而以己意损益之也。”与我们所说的夺胎换骨之用其语而新其意例正相符合。
其实,“夺胎换骨”说本就源于黄庭坚,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换骨夺胎法”条引黄氏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黄氏的夺胎换骨说显然也是从杜甫、陶渊明等人诗歌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悟出来的,但是他对夺胎换骨法的解释似稍欠精准,若以上文绳之,则“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则属用语新意法,《升庵诗话》“杜诗夺胎之妙”措词“夺胎”,即是。“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则属用意新语法,再举《升庵诗话》“夺胎换骨”条为例,有云:
汉贾捐之《议罢珠崖疏》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后汉·南匈奴传》、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全用其语,意总不若陈陶诗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
所举文本分别为奏议、史传、骈文、诗歌,用意略同,而用语迥别,杨慎认为就是夺胎换骨,若析言之,则属换骨法,即用其意而新其语法。
杨慎和张含用杜、化杜的话题,“翻用杜语,新若己出”“用杜而不为杜用”“矜于神而不矜于形”,与自黄庭坚至杨慎的“夺胎换骨”说相通,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对杜诗的学习生发而来,后者是诗歌师法前人的总的原则和技巧,而前者是师法杜诗的原则和技巧。而就技巧而言,主要是两种:夺胎法即用语而新意法、换骨法即用意而新语法。用语、用意是诗歌创作的普遍现象和基本技法,完全的创新不可能,后人学习杜甫,杜甫学习前人,均为必由之路。即以上文所引杜甫《小寒食舟中作》用语而论,除“春水”句外,还有多处用语,如“隐几”系用《庄子》“南郭子綦隐几而坐”,“鹖冠”系用袁淑《真隐传》中人物“鹖冠子”,这是用词,其例甚多,举不胜举。用词当亦属从杜诗抽绎而出的“无一字无来历”之诗歌技法理论。而夺胎换骨法则高出一层,如“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系用沈佺期“云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二句,既有用语,又有用意。林时对认为“云白”句非是“袭”而是“以己意贴之”之“用”,杨慎评张含诗歌“翻用杜语,新若己出”同此例。而“愁看”句亦用古代诗词中常见的“望长安”意象句,但略有新思。以上是用句。因此,宋元明人对杜诗的潜心袭用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仅止于用语用意则非高明,其目的还在于新意新语的“新若己出”。杨慎、张含等研习杜诗之贡献在于此。考虑到当时普遍而浓厚的学杜风尚,杨慎和张含关于学杜、用杜的探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然,杨慎“新若己出”这一创作论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的,如宋王德臣《麈史·诗话》卷中曾云:“古善诗者,善用人语,浑然若己出,唯李杜。”杨慎是用杜甫用语之法而为用杜之法,所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三、真诗史
“用杜而不为杜用”“翻用杜语,新若己出”“夺胎换骨”是联接形式与内容的诗法,但在这个层面之上还有诗歌精神和宗旨等,如“诗史”精神和“风人之旨”,这也是杨慎关于学杜与变杜之要义。
杨慎在评点张含诗歌之前是反对宋人杜甫“诗史”说的,其嘉靖二十年刻《升庵诗话》卷三“诗史误人”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与论诗也。” “诗史”说并不始于宋代,据孟棨《本事诗》“故当时号为‘诗史’”(“高逸第三”)语,可知唐人在杜甫当时即有“诗史”之评。《新唐书》本传云:“甫又善陈时事……世号‘诗史’。”“世号‘诗史’”当本于《本事诗》,而“善陈时事”则奠定了宋人“诗史”说的基本内涵,以后宋人诗话多发挥此论,这正是杨慎批判的靶子。杨慎批判的理论出发点是“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诗经》“其体其旨”究竟为何呢?杨慎接下来论道:
《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是杨慎“性情”论思想的体现,也是《诗经》“其旨”的基本点。但是,杨慎论说的重点却在于“其旨”的表现方式,即“含蓄蕴藉”“意在言外”,这就是《诗经》“其体”的基本点。以《诗经》“其体其旨”为指导,诗歌创作同样要达到“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和“含蓄蕴藉”“意在言外”这两个基本点,这也符合中国古代文论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反观杜诗,其缺失正在于稍欠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杨慎拿《诗经》同杜诗作了比较:“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 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其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 ,可堪皮骨干’也。”杨慎是拿《诗经》含蓄语同杜诗直露语作比较,其实《诗经》多有直露语而杜诗也多有含蓄语,可见其明显的主观之意。但是,这些例子对于表达杨慎的文学观念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最后,杨慎回到对宋人“诗史”说的批判:“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杨慎批判宋人杜诗“诗史”说并非全盘否定杜诗,他否定的是宋人所赞赏的“直陈时事”的杜诗,而肯定的是“含蓄蕴藉”的杜诗。他也并未全盘否定“诗史”说,否定的是“直陈时事”的“诗史”说,而肯定的是“含蓄蕴藉”的诗史说。在这一点上,学界对杨慎多有误解,不详论。杨慎诗话往往抨击宋人诗话,颇有矫枉过正之失。但其现实的针对性则在于纠正前七子派模拟杜诗的不良风气,下文申论。可以说,杨慎“诗史”说也还是有一定积极的现实意义。
杨慎对“诗史”说的赞同可以从其关于张含诗歌的批评中窥见,将其“诗史”之评语罗列如下:
诗史也。(《龙编乱》题评)
此诗真诗史,与韩文公之《汴州乱》、晁无咎之《开梅山》、杨廷秀之《海鳅船》、王恽之《义侠》、《王著行》同传可也。(《宝石谣》尾评)
两绝句为诗史。(《两绝句》尾评)
叙事明畅,可称诗史,非规规学古,顾门面而不切事情者。(《历峰歌为程参伯作》尾评)
从以上评语中可以得出以下看法:第一,此数首诗均可归入“以韵语纪时事”之“诗史”行列,且“诗史”之评非为中性评价而是赞美性评价。第二,第二条《宝石谣》尾评列举可与同传的四家,可见杨慎对历代诗史之作颇为熟稔,着实下过研读功夫,其评价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三,张含的诗史之作艺术特征为叙事明畅切实。杨慎在此并未强调《升庵诗话》发表过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之说。再来看张含数诗的内容,却是杨慎曾批评过的“直陈时事”。如《龙编乱》有“官府如虎吏如狼”“鞭挞流血威穷方”“官廪空虚私室肥”等语,《宝石谣》有“地方多事民憔悴”“驿路官亭豺虎多”“鬻男贩妇民悲号”“涕泪无声肝胆碎” “独怜绝域边民苦,满眼逃亡屋倒悬” “山川城郭尽荒凉”等语,似略同杨慎所批评的“类于讦讪”。同为刺诗的《两绝句》,第一首云:“天上烟云秋寂寥,城中人事日萧条。网罗不见寻麟凤,彩石光珠价恁高。”由末句可知,此两诗主题同《宝石谣》,均为讽刺朝廷和官府疯狂开采云南宝石而造成的民不聊生惨象。第二首云:“黄云黑雾暗边城,虎豹鸱鸮日夜鸣。金甲宝刀旗帜过,两行钦取字分明。”“两行钦取字分明”与《宝石谣》“钦取旗开山岳摇,鬻男贩妇民悲号”同义,所谓“钦取”当指官府打着皇帝的旗号采买宝石,“两行钦取字分明”可作歇后“鬻男贩妇民悲号”看,合上“城中人事日萧条”“虎豹鸱鸮日夜鸣”等语来看,其讽刺之意绝不亚于《宝石谣》。由上述可知,杨慎的“诗史”观发生了变化,由重“含蓄蕴藉”的诗史观发展为“含蓄蕴藉”与“直陈时事”皆可的通融诗史观。这个变化当与杨慎批评的对象变化(由前七子派而张含)以及杨慎因与张含诗学密切交流而互有影响的变化相关。学术界关于杨慎诗史观的讨论亦未关注此一变化。
张含弟张合甚至认为诗歌的首要特征即为史,其序张含嘉靖十四年诗集《乙未鸣》有云:“嗟乎!诗以史冠,史以采硕,诗而弗史,乃言佻式闲美,奚贵焉?”如果诗歌仅有形式之美(“采”“佻式闲美”),并不可贵,而可贵者在于“史”之内容。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张合认为杜诗因其史的特征而贵于古今:“甫子之诗之所以贵于今古者,以采亸而足史焉尔。” “采亸”就诗歌形式言,“足史”就内容言,而后者更为重要、更为可贵。张含“诗以杜志”,当然也确然“史亦蒸蒸”,张合举了四组张含诗歌作为证据(张合《弁乙未鸣》),说明张含的诗歌主要特征和贡献也在于诗史。
但是,诗史并非杜诗专利,若溯其源则为风诗。上引杨慎《张子小言序》在批评前七子派模拟之失后,指出其错误的原因是“此非过乎风人之言,不及乎风人之言也”,即与风诗精神相背离。他认为张含学杜“不矜于形而矜于神”之论“可与言风也已”,即与风诗精神相吻合。以风诗为标准,大概是张含、杨慎之学杜与前七子派学杜之分殊。杜甫之诗史就是继承批判现实的刺诗传统。“矜杜之神”的张含诗歌题中应有之义是继承杜甫诗史精神,而又上承风诗精神,因此“可与言风也已”。上述议论符合杨慎一贯的由杜甫上溯《诗经》的文学理论和论诗策略,其《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有云:“永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杨慎说:“十五国诗也,孰命之为风乎?懿哉,其称名也。风以声动物,诗之音感人,一也。声由音也,音由声也,风由诗也,诗由风也。”风与诗是类比的关系:“风以动物”与“诗以感人”。感人就是诗歌的本质,风诗就是感人之诗,因之成为诗歌的最高典范。杜诗即于此而相通于风诗,由杜诗上溯风诗的理路也就在于此。
还需说明的是,学习杜诗、学习风诗,并不是要写成杜诗、风诗,而是学习其精神,成为自家之诗。那么张含诗歌的审美追求和总体特征是什么呢?是“滇风”,即反映一时一地的云南风土人情之诗。张合《弁乙未鸣》概括出张含诗歌“史亦蒸蒸”的特征后指出:“固一于兄近所造,而其可以为史也,则有大者在焉。……使得如古之陈于太师焉,闻于元后焉,不几乎为滇之风乎?”所谓“陈于太师焉,闻于元后焉”者指的当然是国风之诗,那么张含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就是继承国风传统的“滇风”。张含也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其《朝暮》云:“作诗岂徒苦,甚欲成滇风。”可见,张合的意见略同于其兄,也可以说是杨慎和张氏兄弟的共同理论追求。
四、少陵之变
杨慎“永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说事实上就是学杜而变杜论,这里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学古(如学杜),一是变古(如变杜)。学古是学习古人诗歌艺术,变古是以己之情变古之情,学古是手段,变古是目的,即从古人汲取诗歌的养分和艺术以表现作者的真情。
杜甫是古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在古体继续发展、近体接近成熟的时代,其诗转益多师,各体兼工,具有集大成性质。因此,学习杜诗是锻造诗艺的必由之路,这个认识是由宋人至明人渐次确立的。特别是在明代前后七子派盛行的时代,学杜风气最为浓厚,甚至成为学诗的不二法门。茶陵派也推崇杜诗,其领袖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对杜诗艺术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推动了杜诗学的发展。但是,前七子派崛起京城诗坛后,为夺取茶陵诗派的主导地位,遂采取了批判茶陵派的姿态。若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为观察视角,茶陵派属保守派,而前七子派属激进派,如李梦阳等就讥讽李东阳“萎弱”,这既是指李东阳政治上的“萎弱”,也是指其文学臣服政治的“萎弱”。以学杜为例,前七子派就更多地继承了杜诗批判现实的创作倾向。刘瑾乱起,茶陵派与前七子派由文学斗争演变为政治反目,前七子派纷纷遭到排挤,渐趋于消歇。彼时,杨慎虽为李东阳弟子,但尚未及第而入翰林苑(阁臣培养之所),且与前七子派多有交游,因此他并未站队而进入两派的文学、政治之争。不过,杨慎此后借由批判宋人杜甫诗史说,实则有批判前七子派“直陈时事”“类于诘讪”之嫌,似为偏袒台阁派者。杨慎被贬云南后,与曾为前七子派领袖李梦阳弟子的张含交游频繁,境况发生很大变化,遂超然于文学流派之争,秉持博学的学术理念和“向上一路”的诗学理念,确立了“永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的理论主张,博学自杜甫溯至《诗经》历代各家之诗,这也符合读书万卷、转益多师、各体兼工、集诗大成的杜诗特质,进入学古以变杜的阶段。张含深受杨慎影响,反映在创作之中,而杨慎之评点予以抉发,在一定程度上标识杨、张诗学之共同体。
杨慎《张愈光诗文选序》即发为诗文“稽古”之论。“稽古”有三个层面:言、行、道。《孟子》所谓“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就言及言、行、道三个层面。可见,所谓的“道”就是尧舜之道,也即儒家伦理之道。这三个层面是统一的,是不朽者必由的三个进阶。韩愈言曰:“好古人之言,好古人之道也。”言及言、道两个层面,而此“言”转入文学层面。据上,杨慎的结论是“言之不可不稽古也如是”,这里的“言”当然也主要指文学。张含就是“博极群书,肆力于古”者,他的诗歌“上猎汉魏,下汲李杜”,杨慎所编《张愈光诗文选》即其“稽古之效”而“必其传”者。张含“工于求古”,其目的是“行古道于今”,“盖其道有与古合者,其言之似古也原夫斯”。杨、张之文学“稽古”论可谓“嗜古”“博古”者之学古论,同前七子派中的拟古论略有“不蹈袭”与蹈袭之区别,上已言之。
杨、张博学之中又有重点。杜诗与《诗经》之间可分汉魏与六朝初唐两个阶段,汉魏诗浑然不可句摘,气象可感而诗艺难达,前七子派主张古体学汉魏,但多有流于腔调者。杨、张之派有惩于此,另辟蹊径,提倡学习六朝初唐。杨慎《五言律祖序》言其编选动机曰:
寻滥觞于景云、垂拱之上,著先鞭于延清、必简之前,远取宋、齐、梁、陈,径造阴、何、沈、范。
景云、垂拱为初唐年号。宋之问字延清,杜审言字必简,均为律诗成熟之完成者。可知,杨慎明确主张学习六朝初唐。其理由是六朝初唐诗是盛唐诗的“先鞭”和“滥觞”,杜甫为“诗宗”,也专力学习六朝初唐,那么学杜者也必学六朝初唐。前七子派较为忽略对六朝初唐的学习,可见,杨、张六朝初唐派诗学思想更为通融,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
张含诗歌博学众体,因受杨慎六朝诗学影响,颇专力于学习六朝初唐。如其《效鲍体数诗》系学鲍照的数字诗,而其《新体闲咏》系效六朝叠字句法,可见其与杨慎均有博学好奇之习,而又于学古之中颇有变化,是学古而变古,因此为后者所激赏,不详论。而我们更关注的是张含学古而变杜之作,如其《虎丘歌席赋得当歌共衔杯》诗系学徐庾玉台之体:
金缕度歌头,锦筵云色流。杯分鹦鹉共,曲合凤皇求。眼波含月懒,脸晕逗霞羞。倚烛颓嵇玉,偎香藏弋钩。
杨慎评曰:“亦视徐庾。”此诗写男女之情而隐寓君臣相遇之期许。杜诗绝少男女之情和寄托之意,而这正是杨慎、张含派欲以六朝弥补杜诗不足之诗学主张。初唐诗也善写男女之情,当然在杨、张崇尚之列,如张含诗《离夕有赠效垂拱体》云:
仙子武陵溪,春深归路迷。翠翘迎露湿,罗袖避风啼。留佩花笼玉,分钗月印犀。金杯延落日,酒醒各东西。此诗以男女分别之情写朋友分别之情,缠绵悱恻,而惜别情深,为初唐体。杨慎评曰:“近世学杜而此样风致刬尽,盖亦偏矣,善诗者必兼之。”卷二亦为以初唐诗之“风致”(即男女风情)补足杜诗之偏论。垂拱为唐武后年号,名以为体,少见,当指四杰、沈宋成熟时期之律体。
又如张含《独步》诗云:
青竹园中独步,翻云淹竹溪流。春花一开双泪,春鸟一啭千愁。
杨慎尾评云:“尾句似六朝,知者可语此。”“尾句”当指“春花”“春鸟”两句,“似六朝”者当用隋柳《阳春歌》诗首两句“春鸟一啭有千声,春花一丛千种名”语,此两句兴起下文之愁思:“旅人无语坐檐楹,思乡怀土志难平。唯当文共酒,暂与兴相迎。”张含诗“双泪”“千愁”当与“志难平”同意,均为怀才不遇之闲愁。我们也可以说张诗此两句未必不用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语,两者均以春花、春鸟各为一句,而“双泪”对“溅泪”,“千愁”对“惊心”。不过,二者表达的情感有别,杜诗为“感时”和“恨别”。张含此诗通过学六朝和学杜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学古以变杜和学杜以变古的双向目的。
上举张含《离夕有赠效垂拱体》及杨慎评语还涉及杨慎所提出的“律含古体”“律含古意”“古律”之诗学主张,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古体学习六朝初唐其理自然,但律体学习古体就颇为特别。此诗婉丽,不脱六朝绮丽风致,可谓“律含古意”者,杨慎认为学杜者“必兼之”,亦可见杨、张学习六朝初唐之敏锐和深细。又如张含《为升庵题昭君障子》五六句曰:“云貂笼髻出,冰[XC雷磊字2]隐鞘鸣。”此两句用语雕琢,对仗精工,而又颇能状冰雪奇寒气候下人马跋涉艰辛之状,以此衬托昭君出塞极度凄凉之心境。杨慎评曰:“五六不止为奇律,可入颜谢辈古选,知者自信,难语俗人。”即以为可与齐梁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精警之句相媲美。律诗格律谨严,讲究练字练句,当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六朝诗歌学习,以达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艺术新境。古体与律体诗艺之相通于此可证,而前七子派割断盛唐与六朝初唐血脉相连之关系颇为不智。又如杨慎评张含《春日过武陵》诗“驰驱六身懒,忧患二毛新”两句云:“ ‘二毛’‘六身’,工致似庾开府”。与上诗之评同一用意,即要求律诗应向六朝古诗学习,既学其精致,又着其古意,则臻古雅之高境,与前七子派追求“格高调古”的审美理想是不约而同的。
与此相反的倾向则是作律诗而学习晚唐之绮丽,这是杨、张等所反对的。如张含《无题》云:“维摩丈室散花回,公子华筵向晚开。锦里词华薛洪度,秦川歌舞赵阳台。颓云宫髻笼香界,纤月城眉照玉杯。舞罢罗裳小垂手,一枝豆蔻薄寒催。”然此“豆蔻”乃六朝初唐之“豆蔻”,而非晚唐杜牧之“豆蔻”,系写艳情(即男女之情),而非色情。因此,杨慎评语曰:“绝似初唐,无论西昆也。”特意予以提醒,以免误解杨、张提倡的六朝初唐之主张。张含《游龙溪古寺同李仁甫》云:“天畔丹霞翠壁开,山灵应讶远人来。花宫日月遥观海,香界金银晚上台。忍草禅枝牵倚仗,白鸿黄鸟弄衘杯。暮年词赋空奔走,不尽江干庾信哀。”杨慎评曰:“缘情绮靡,律含古体。” “缘情绮靡”是六朝诗之总体特色,则杨慎之意就是律诗应当从内容(“缘情”)与形式(“绮靡”)两个方面向六朝诗学习,这就是杨张派之诗学宗旨。
律诗之宗者为杜诗,同张含《离夕有赠效垂拱体》诗及杨慎评语一样,“律含古体”或“古律”有针对学杜而发者,是欲兼六朝初唐与杜甫之长。这也就是杨慎、张含所主张的“少陵之变”的主要内涵。杨慎六朝派(或六朝初唐派)主要成员除云南时期的“杨门六子”外,还有京城时期的薛蕙等。
总之,杨慎的张含诗歌评点是代表杨慎晚期文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为《升庵诗话》的有益补充,而学界讨论杨慎文学思想多据《升庵诗话》而少涉及于此,由此可见其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杨慎杜诗学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明汤宾尹《春居集杜序》云:“夫杜与我相为用,而我与杜不相为用。”即发挥杨慎“用杜而不为杜用”之说。清杨伦《杜诗镜铨凡例》亦云“能继迹风雅,知此方可与读杜诗”,即认同杨慎“效杜陵以上四始”之论。清乔亿《剑溪说诗》认为学杜当“从六朝入更无气粗之弊”,则暗合杨慎六朝诗“先鞭”“滥觞”之说。
文献引用格式
雷磊,臧洁.明代杜诗学中的学杜与变杜——以杨慎评点张含诗歌为中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3):102-111.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王蓉)
【来源:湖南师大社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