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后政治时代解放政治的重构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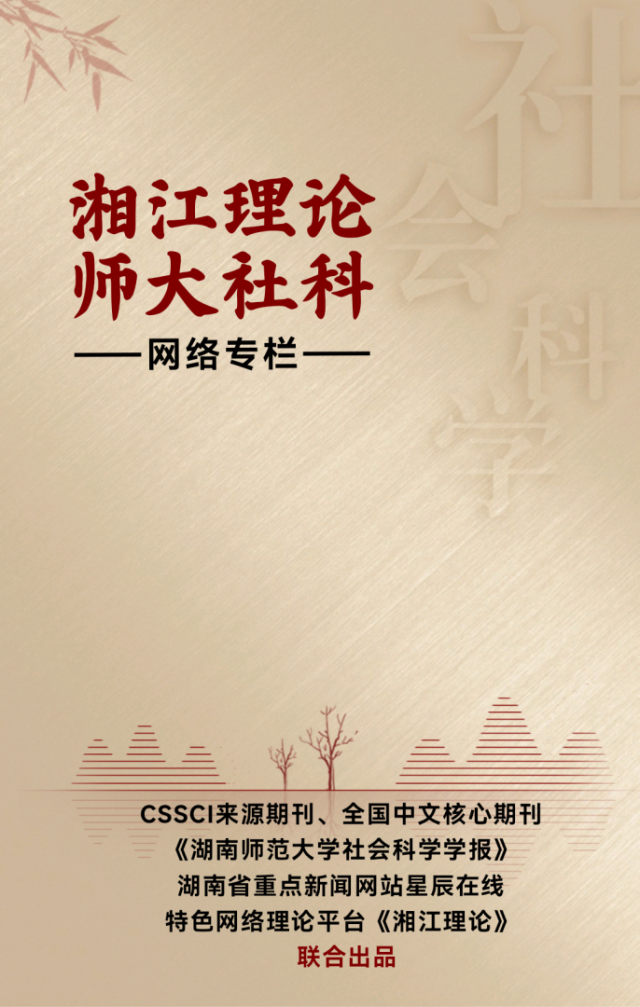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史凤阁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后政治时代解放政治的重构
——兼论齐泽克的行动哲学
核心提示
齐泽克将当代资本主义诊断为政治终结的“后政治时代”,这是一个象征建制效力瓦解、宏大叙事终结、政治蜕化为日常治安逻辑的时代。在后政治时代,多元文化主义取代意识形态冲突,以一种政治进步之姿呈现在世人眼前。然而,齐泽克将多元文化主义指认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理想意识形态。在对多元文化主义批判的基础上,齐泽克着眼于解放政治的重构,在融合拉康式驱力主体观、列宁革命观的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行动哲学。这种行动哲学以死亡驱力重塑了后政治时代的革命主体,以巴特尔比政治拒斥了西方大多数左翼的伪行动策略,以列宁式决断行动重新勾勒了后政治时代的解放政治轮廓。
内容精选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政治体制被视作一切政治议题的讨论前提,阶级斗争被视为宣扬暴力的、行不通的方案被自动排除。齐泽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取消了政治面向的“后政治时代”,亦即剥夺了“政治热情”、对真正的政治进行否认的时代。面对这一政治情境,如何找寻新的革命主体、擘画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齐泽克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后政治的本质特征的同时,敏锐地洞察到自由主义左翼多元文化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并对其提出了有力批评;与此同时,齐泽克以拉康式驱力主体观为基础,建构了其特有的行动哲学。齐泽克的行动哲学致力于重新标举普遍性政治,以革命之姿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可以说,齐泽克的行动哲学有力冲破了“后政治时代”政治终结的困境,重新激活了“政治”,为左翼重构解放政治、探索新的革命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资本主义后政治时代的三重规定
“后政治”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标识,它又被称为“没有政治的政治”或“政治终结的政治”。在这样的时代,象征秩序不再成为人们生存意义上的终极担保,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被消解,有关人类幸福和解放的承诺被开明官僚的技术统治取代,资本主义仿佛也被默认为将长期存在,“政治”也因此在西方内部被消解。
首先,后政治时代是大他者瓦解的时代。齐泽克提出我们正处在“后现代式的后政治”。要准确界定后政治时代,须对后现代有一个基本认知。“后现代”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它指向人类理性自我发展中的悖论性,即理性自我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他者的瓦解,即“社会建制、习俗和法则的公共网络的最终瓦解”,这意味着象征建制效力的衰微。因而,当提及“大他者的瓦解”时,这意味着“我们作为成员之一的那个团体已经解散了”,也就是说,人们不再信任大他者,后现代社会的自反性风险导致社会的发展变得不透明和不可测知,再也“没有一个自然或传统可以提供坚实的基础来让我们依靠”。
其次,后政治时代是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终结的时代,它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种变体。后政治主张“搁置意识形态纷争,抛弃旧的冷战对立思维,主张合作与多元共存”。即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像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样伟大的意识形态规划的意识形态时代结束了,因此我们已经进入了理性协商和决策的后意识形态时代,所依据的就是对经济的、生态学的等等必要性的中立洞察”。伴随后政治时代到来的是人们政治热情的衰减,在后政治时代,意识形态对抗的宏大叙事已不再可能,具体而微的特殊议题广泛兴起。
最后,后政治时代是政治蜕化为对日常事务管理的治安逻辑的时代。在齐泽克看来,后政治“不再只是‘压抑’政治面、企图控制它并平定‘被压抑者的重返’,而是更为有效地去将之‘取消’”。这导致“由竞逐权力的各种政党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被替换为开明的技术官僚(经济学家、民意专家……) 与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政治变成了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技艺。对后政治视域下政治的本质,齐泽克借用朗西埃提及的“政治”与“治安”之区分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朗西埃看来,“治安”遵循一种稳态有序的逻辑,旨在维护社会在治安秩序内的稳定运行;“政治”则与“治安”根本对立,它是对治安构序的一种中断,它以一种异质性的无分者之分的角色,介入并“破坏治安秩序的感知分配”,这种无分者之分争取言说的权利,并努力实现与其他看得见的部分之间的平等。以这一区分为基础,齐泽克提出了当下资本主义处于非政治化的后政治时代,即可感知者各安其位、普遍性政治面向褪色的时代。
二、进步政治的幻象: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及其批判
在后政治时代,多元文化主义被标示为所有进步思潮的共识,并演化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性,成为我们探讨所有议题的不可挑战的预设。齐泽克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发挥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补充作用。
首先,多元文化主义是契合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理想意识形态形式。齐泽克认为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开启了一种“只有殖民地,没有殖民国”的自我殖民体系,在跨国资本运作下,“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大都会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对立;全球性的公司,仿佛已经切断了与母国之间的脐带,而且认为自己的来源国不过是另一个有待殖民的领土”。在资本增殖逻辑驱动下,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契合这种无根的、流动的跨国资本的理想意识形态形式,它尊重差异的表象背后,所捍卫的正是“资本”这个大写的“一”。多元文化主义所掩盖的正是这种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权力的加强,并因而成为跨国资本同质化运作的有益的意识形态补充。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自我指涉的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宣称尊重差异、包容他者,但仔细剖析,我们会发现,多元文化主义的底色是欧洲中心主义,其本质仍是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采取普遍性的立场,它将自身的实存内容全部掏空,保持中立的立场;正是在这种姿态中,多元文化主义“将这个位置保留为一种占有优势的普遍性空白点,可以从这个位置出发去妥切地欣赏(或轻视)其他文化”。这种审视性的姿态,使其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因而,“多元文化主义者对他者的特殊性表现的尊重,其实正是一种标举自己优越性的形式”。多元文化中心体现了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性而与自身所宣扬的包容、尊重相背离。
最后,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精英式的意识形态,它体现了西方左翼与底层人民之间的割裂。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内部,以一种精英、中上阶层享受差异的体验,彻底暴露了其与社会底层的割裂。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倡者多为中上阶层的学者,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去称颂后现代式移居主体的杂种性,认为他们不再依附于特定的族群根源,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自由流动”。这种自由穿梭、享受差异的体验只不过是秉持世界主义的中上层学者的专属特权;我们还应看到那些穷困的移民劳工,所谓的自由流动对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创伤性体验,他们更不可能在这种出走中去体会自由流动的解放性力量。多元文化主义忽略了这种社会阶层的根本差异,并因而蜕化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暴露了西方左翼与底层的真正割裂,无法成为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最终只能沦为资本主义秩序内的一种话语游戏。
三、走向“新解放政治”的行动哲学
在多元文化主义中,主体陷入了欲望的循环,囿于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提供的话语斗争中。要突破后政治困境,关键在于“将标举普遍主义等同于一种投入斗争的战斗性、分歧性立场”。齐泽克指出,拉康的死亡驱力为锻造革命主体开辟了空间。在此基础上,当代左翼应该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成的各种流动性认同中回撤出来。齐泽克基于拉康式主体观建构了行动哲学,为有力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首先,行动哲学的革命主体是一种驱力主体,它的生成奠基于拉康的死亡驱力观。齐泽克对死亡驱力的阐释,始于他对两种死亡之间的区分,死亡驱力的空间处在符号性死亡与真实的死亡之间。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这个处在‘两种死亡之间’的位置,即崇高美或者可怕的怪物所处的位置,正是原质的场所,是处于符号秩序中间的实在界一创伤性内核的立足之地。”这一创伤性的位置暗示着象征化的失败,开辟了一种毁灭和颠覆整个象征秩序的可能空间。齐泽克将拉康的死亡驱力与现实的政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关联,他所看重的是死亡驱力那涤荡一切、颠覆现存秩序的破坏性潜力。正是在主体之驱力维度的层面上,齐泽克看到了激进政治革命的希望所在。
其次,齐泽克借由“巴特尔比”政治的“以退为进”,为新的解放政治开辟革命空间。巴特尔比的“我宁愿不”以纯粹的拒绝之姿否定了符号秩序为主体预设的整个空间,“通过一个纯粹撤退的姿势[用马拉美的话说,什么都不会发生,位置原封不动(rien n’aura eu lieu que le lieu)],使出现暴力的位置保持开放状态”。齐泽克认为当今左翼要中止那种错误的力比多投入,在他看来,当今左翼以直接行动、做点什么的轻率号召“把我们卷入一项活动中,在那里,事物发生改变是为了维持整体不变”。齐泽克认为要进行一种革命性的改变,“就是从行动的强迫冲动中抽身而出,就是‘什么也不做’——这样便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活动敞开了空间”。巴特尔比式的拒绝清理了革命的场域,它让我们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以一种暴力形式打开了一种可以改变象征秩序坐标系的真正行动空间。
最后,在齐泽克看来,要在后政治时代重塑新解放政治,当代左翼要重述列宁式的决断行动。在齐泽克看来,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抓住革命的历史瞬间。面对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复杂形势,列宁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瞬间,促成真正变革现存秩序的行动。当代左翼必须去学习、重复列宁那抓住历史瞬间的革命姿态,唯有如此,才能不再囿于僵化的客观阶段与虚假的民主程序,才能超越并打破旧有的历史进程,并为创造新的解放政治开辟空间。
重述列宁式的决断行动要真正忠诚于行动,勇于承担革命的一切后果。齐泽克认为真正的行动中都包含某些“恐怖成分”,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接受最终的自我毁灭的必要性,为革命的真正完成牺牲自己。他认为,与列宁的敢于担责相比,当代的自由左翼并没有这种责任担当,他们对激进革命的行动抱以深深的疑虑,认为革命行动可能带来更糟的结果。面对这样的疑虑,齐泽克指出真正左翼的忠诚表现在“忠于(革命)原则的完全实现所伴随而来的后果”,一个真正行动的大无畏之处就“在于它完全承担起这种‘每况愈下’”。
重述列宁式的决断行动要求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的过程中标举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齐泽克对资本主义自由选择悖论进行了批判,驳斥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性,并阐释了当今左翼应该坚守的自由——阶级革命行动的自由。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以一种霸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排除了根本性、决定性的选择,留下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选择,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既有坐标体系之内的选择。齐泽克认为,当今左翼真正需要的自由选择,应该是列宁那种确保根本性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恰恰是我们界定一个行动是否为真正革命性行动的判断标准。
结语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后政治时代,当代左翼面临着一种政治终结的困境,这种终结并不仅仅是对政治的压抑,而是借由各种意识形态工具对之更为有效地取消。在这样一个时代,象征建制不再有效运作,人类解放的宏大议题也不再有大他者的担保,意识形态冲突也逐渐被多元文化主义取而代之,它以政治进步的面貌呈现,其发声领域被局限于身份、族裔、生态等微观议题,在对差异性政治、族裔认同的参与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共谋,其不断增生的议题成为给养资本主义系统的可口肥料。面对如此困境,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旗手齐泽克准确把脉后政治本质特征,有力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并破除其政治进步的幻象,在借用拉康式驱力主体观、借鉴列宁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行动哲学。齐泽克以死亡驱力重塑了后政治时代的革命主体,以巴特尔比政治拒斥、破除了左翼伪行动策略,为革命的暴力降临开辟了空间,以列宁式决断行动重新勾勒了后政治时代的解放政治轮廓。齐泽克的行动哲学重新激活了当代左翼对解放政治的探索,对当代左翼冲出后政治时代的政治终结困境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文献引用格式
史凤阁.后政治时代解放政治的重构——兼论齐泽克的行动哲学[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3):141-148.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李彬)
【来源:湖南师大社科学报】


